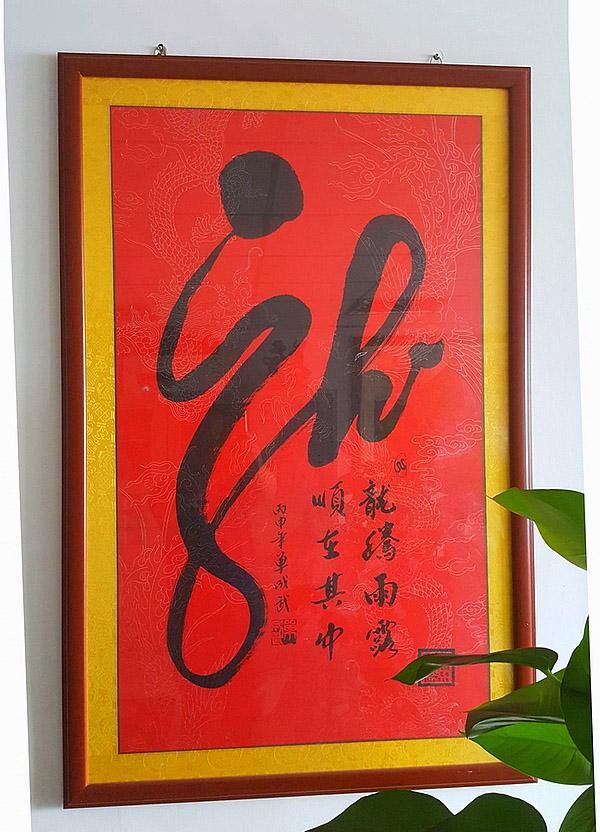文 / 罗 旦
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这块石头来自海子的短诗“西藏”。有人说海子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浪漫主义者、“狂人”式的先知、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三百多年前,孤独的石头上,或许就坐着这么一位诗人,漫天的星辰是他的听众。他的形象时而知性,如“雪域高原最神秘的诗人”;时而浪漫,如“最长情的佛陀弟子”;时而桀骜,如“离经叛道的情僧”;时而凄哀,如“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总体而言,仓诗(姑且称之“仓诗”)平淡自然却韵味醇厚。仅以大家最熟悉的“玛吉阿妈”为例。有些读者认为“玛吉阿妈”是诗人禅定冥想中的本尊化见,“圣美纯净、哀感顽艳”,因此是宗教情怀的道歌表达;有些读者坚信“玛吉阿妈”意指当时尚未降生的第七世达赖喇嘛,因此,这首诗歌是“深蕴政治斗争史实的抒情作品”;还有一些读者笃定“玛吉阿妈”指代他的情人,仓央嘉措诗歌是男欢女爱之情歌,一些“有想法”的读者甚至跑到玛吉阿米餐厅“守株待兔”。
近年来,随着对仓央嘉措研究的深入,某些学者甚至提出仓央嘉措是如同更敦群培般“疯智文明的典型存在”。如此这般的讨论从未停止。萧蒂岩先生对仓央嘉措有个经典评论:“位居僧俗之上、名入情网之中、神游爱海之外、载誉地球之巅而又为唱其歌、译其文、论其志的人尚未完全理解的六世达赖”。
毋庸置疑,仓央嘉措诗歌为后世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以及各类任性阐释。恰如黑格尔所言“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为矛盾的意志”。不过,今天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热爱与研究,未尝不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日益丰润、文化自信日益增长的雅致呈现呢?
恐负如来不负卿。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深受佛教价值观影响的民族,对这样一位有些反传统、反道德、反常规,不断打破禁忌,甚至一度被废黜的达赖喇嘛,不仅没有义正言辞的质疑 ,几百年来,反而催生出对其存在境界的感悟与理解,对其气节的接受与仰慕。
先来看看这两首:“观修上师相,未入安住境;乍见俏娇颜,挥之而不去。”还有这首:“布宫圣至尊,仓央嘉措师;逻些浪迹者,唐桑旺布汉”。
这两首诗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位仓央嘉措的坐标,即宁做有血有肉、七情六欲之“人”,而非高高在上、藐视一切的“神”,阐发了朴素的人文主义观点。诗歌时隐时现地透露出诗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否定并反对愚昧迷信神学思想的倾向。要知道,仓央嘉措所处的时代,欧洲刚刚经历“文艺复兴”。仓央嘉措的诗歌,尽管已不觅音符、不见曲谱,其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宗旨,又何尝不是东方版的“神曲”呢?
梦里寻“她”千百度。三百多年来,袈裟诗人仓央嘉措超凡的人生韵味、洒脱的生命境界,以及展现独特人生体悟、生命关怀、真理探寻的诗风诗境依然是今天我们前行时忽明忽暗、忽隐忽现,却总不消逝的灯塔。
“皎月东山顶,如如妙止观;映入谁娇容,是那未生娘”。这首世人耳熟能详诗的最后一句“མ་སྐྱེས་ཨ་མ”被于道全先生创造性地翻译为“未生娘”,而“未生娘”从字面理解即未曾生育而被称为母亲的女子。作为释迦牟尼的弟子,仓央嘉措一定会将佛教的观点映射在诗歌中,因此,“未生娘”可能就是“空性”理念创新性的具象化。按照佛学理论,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甚至连“无”都没有,即“空性智慧”。佛学家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东西,即无自性,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即无常,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起,即“缘起性空”。这个理论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样,试图探究宇宙之本初。有趣的是,这种理论和唯物主义的事物普遍联系、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等还真有一定的相通性。
不难看出,诗人对人生的极致体验,对宇宙真理的开拓性思考,使他白话般的诗歌具足灵性的同时,不怠慢探求真相的初心。
“逻些人如潮,琼结人若玉;余之梦中人,温润似瑾瑜。”
此诗从字面上理解,诗人貌似平平无奇地提出了人品第一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爱情择偶观。不过,因循守旧绝不是诗人的风格、好为人师更不是诗人的一贯路数。那诗人缘何将逻些和琼结两个似乎没有太多必然联系的地点做一个对比呢?翻阅文献、追寻谜底,不难发现仓央嘉措的前世——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竟然就出生在今山南市琼结县,坐床在拉萨哲蚌寺,后被顺治皇帝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诗人的“意中人”难道暗指的就是第五世?仓央嘉措,“放浪形骸”,却被藏族人民接纳为达赖喇嘛;益西嘉措,“正襟危坐”,却是拉藏汗蒙古势力拥立的傀儡。到底谁才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呢?可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吾辈仅是蓬蒿人。仓诗总是能不经意间地让读者在平实中见深意、在市井中觅高贵、在缠绵中话真谛,既有百转千回的坎坷,又不乏柳暗花明的豁然。
“小女自侯门,深闺初长成;汪汪似蟠桃,坠坠压枝头。”
这首诗翻译过程中,总是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随着翻译的曼妙递进,笔者不经意间掉入了香山居士“长恨歌”的意境。那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更是让两位相隔近千年的诗人在此刻相遇、相知。诚然,两首诗存在长短诗等诸多区别,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字璧坐玑驰,声调悠扬婉转,常读常新。不同于唐明皇后宫三千佳丽、天下美女唾手可得的特权,仓央嘉措身份尴尬,既没有正式坐床为“神王”达赖喇嘛,又只是受了比丘戒的普通人,对于爱情的渴望却生生地套上了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桎梏。或许这恰恰还原了当时农奴制社会的真实场景: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等级森严、践踏人权;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因而,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爱情只能被憧憬,平等只能被向往,自由只能被奢望。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那时苏联已经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马丁·路德·金已经在美国开始轰轰烈烈的反歧视运动,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刚刚诞生,而此刻西藏不到人口5%的农奴主阶层,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95%由农奴构成的底层老百姓却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下面这首诗何尝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控诉呢?
“往生坠地狱,阎王持业镜;阳间多不平,阴间求秉公。”
乍一看,上一首是爱情诗,这一首诗就变成宗教诗了。其实,诗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抨击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是第二首以“阴间”“阳间”做对比,诗人面对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景,以“神王”之尊“大逆不道”地代言底层人民,近乎绝望地呼唤爱情、渴望美好、抨击不公,彰显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呵斥丑恶的社会担当,再现了诗人金刚怒目的善良坚定。
假去真来真胜假。仓央嘉措诗歌既有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对佛法修行的初心、对至纯友谊的歌颂、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更有对社会阴暗面,尤其是对世间乱象毫不惜力的鞭笞。
“乌云镶金边,酝酿霜与雹;戒衣藏俗欲,欲毁佛与法。”
这首诗将世人的目光拉回诗人身着的袈裟。佛教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与时俱进应当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担当。显然,诗人所处的时代并不美好,诗中所描绘的“非僧非俗”之人,应该是影射宗教界一些乱象吧。这首诗对于今天同样有现实意义,诸如“朝阳区30万仁波齐(切)”的笑谈、“王兴夫、杨洪臣”的假活佛案等,再次让人联想到释迦牟尼所说: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一位佛教徒告诉笔者说他绝不会见到穿袈裟的就拜,这种“依法不依人”“去伪匡正正信净信”的态度可能正是此诗的真正用意之所在吧。另外,对于“活佛转世”,宗教仪轨、历史定制、中央批准,毫无疑问是最根本的遵循。至于“假仓诗”,诸如:《见与不见》、《问佛》、《十诫诗》等仿作,笔者认为无需太过介意。的确,这些诗都不是仓央嘉措本人作品,有些完全是杜撰,但无伤大雅。即便明知是仿作,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愿意把它当成仓诗,当然可以理解为人们向往和追求文明、和谐、美好生活的一种表现。
“老獒美须髯,聪慧更胜人;莫言黄昏去,莫言拂晓归。”
偷偷去会美人,却顺带把看门老藏獒任性地调侃了一番,要知道青藏高原的人们往往把家里的狗也当成家庭成员来对待,诗人赋予老狗以人的生动与尊严。借此诗,巧妙彰显出众生平等、守望尊严的朴素价值观。不过,结合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权力时时处处限制诗人自由的,只有摄政第司·桑杰嘉措,难道躺枪的就是此人?的确如此,表面上看,诗人似乎对他限制自由颇有不满,并进而谐谑了一番,可真的对其“人肉搜索”一番,才发觉诗人的不满另有深意。具体来说,诗人前世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司·桑杰嘉措没有将这一重大变故向清朝中央政府汇报,反而秘不发丧,秘密寻访第六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诗人一生的坎坷与磨难。回头再看,如果当年第司从一开始坦坦荡荡向康熙皇帝报告五世达赖圆寂、寻访、转世的真实情况,求得中央政府的认可,或许,仓央嘉措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吧?
劝君更进一杯酒。“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是青年徐志摩道别康桥时流动的诗词画面。不知何故,它总能把我拽回600多年前仓央加措送别友人时的场景中:“圆帽扣发顶,柳辫身后甩;道声请慢走,回句君留步;诉声离别苦,告句待相会。”
毫无疑问,这首离别诗是仓央嘉措诗歌主题的扩展和丰富,一个以友谊为线索,勾勒出友人“去去天涯无定期”的难舍,以及诗人“悲莫悲兮生离别”的苦楚。这种平平常常的别离,居然也成为袈裟诗人的诗歌主题。尽管文字平平淡淡,没有奇句可觅,但诗人正是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将丰富充沛的思想倾述出来;文字的“简”与内涵的“满”相得益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不过对于这首诗,一些读者认为是男女恋人分别的意境,爱情的成分多一些。的确,从藏文表述来看,无法确定道别对象的性别,也看不出两者的关系。不过纵然是美女,即便是爱情,这种伤别离的质朴、直接,让人泣、令人悲。有别于白居易“不得哭,浅别离;不得语,暗相思”的不可名状之苦、不可表白之痛,仓央嘉措的道别千般不舍,香山居士的别离则万般无奈。
不过,在诗歌的创作,香山居士与仓央嘉措都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道,所以,清代刘熙载对白居易诗词的评价好像同样适用于仓央嘉措的诗歌:“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述不完情本无情,道不尽缘本无常。“执象而求,咫尺千里”,对于仓央嘉措诗歌的诠释,对于本人情感的真实再现,诚然不免盲人摸象,不及万一,正如和他同一个时代的纳兰容若,一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何尝又不是对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的真实写照呢?不过,同世人多分享一个解读的维度,多摸索一个如此诗人的这般解读,岂不美哉?岂不妙哉?

作者罗旦,藏学博士、文化学者、诗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兼职教授,2013年中国藏学家赴欧洲代表团成员,长期从事汉藏英国内外教学工作;数次担任国际性学术会议英文翻译,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汉、英学术论文,主持并参与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重点课题研究已出版数部藏学书籍。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 | 悦读频道
| 悦读频道